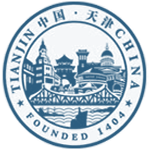提起中国传统社会的“家礼”,人们的脑海里通常会浮现深宅大院、威严肃穆的情景,或是祭祀祖先、祠堂的摆设,但实际上,历史上的家礼还包含了这样的内容:早上天刚亮,子女就要起床,打扫室内外卫生;洗漱完毕、穿戴整齐之后,要到父母卧室门口,低声询问他们昨晚睡得好吗;要是休息得不好,就要找原因、想办法;如果父母身体不适,有痛痒的症状,就得马上帮着解决,不能置之不理。父母如果有事儿呼唤,做儿女的要快步跑到父母面前应答,但不能太快,冲撞了家人。儿女做其他的事情,例如外出,也要及时告知父母,免得他们担心。
上述做法,出自我国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书《礼记》中的《内则》、《王藻》两章,从中可以看出,传统家礼文化对家庭成员言行的规范或习惯养成的约束,古今大体一脉相承。
其实,在家庭里或家族内,有些事情能做,有些不能;有些虽然可为,但会不太合适;而有些言行就非常合乎自己的身份与所处的氛围,会受到称赞。对此,如何判断,怎么权衡,我们会考虑,古人也会思量,而且古今差别不会太大。但我们似乎又难以对所有的规范都条分缕析,列出个一、二、三。其实,那些对在家言行的规则,很多就是传统家礼文化的一部分,属于行动上仪式性色彩比较强的“礼节”。
对这些规定,古人却并不模棱。在形式多样的家礼文本中,可以读到许多具体的家礼内容,这属于“礼义”。礼义就是在道理上对所该做和不可为事情的解释。它们有的针对一家一族,有的更具普遍性,可供别的家庭参考借鉴;有的就事论事、因人发言,有的自成系统,包罗广泛;有的重在训诫和规劝,有的还包含仪式,兼有示范性和操作性。因为内容多样,家礼著作的名称也难以严格划一,家训、家规、家范、家诫、女教、童蒙教育等,其实都属广义的家庭礼仪范畴。可以说,礼节和礼义是构成中国传统家礼文化的一体两面,也就是构成中国“礼仪之邦”中的“礼”和“仪”这两个元素,目的都是令人的言行中规矩、合道理。
但这规矩、道理究竟从何而来,与“国法”又有什么联系呢?这要从源头上看。对礼是如何产生的,看法历来不一,大体分为源于祭祀、本诸人情和出自风俗三种,但都认为礼来自社会现实,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连,旨在确定生活中的原则和秩序。因此,“礼”对“法”有十分重要的影响,只不过两者管辖的范围不同,因此我国历史上有“礼施行于未然之前,法施行于已然之后”的说法,也有“礼主法辅”的观点。
拿我国现存最早的法典《唐律疏议》来说,后世学者称它“一准乎礼”,就是一切以礼为准绳。清代大学者孙星衍的说法更明确,他在重刻这本法典的序言中谈到“律出于礼”。也就是说,在中国传统上,国家法典是从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礼中脱胎而来。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:将法律史上影响最大的《唐律疏议》和礼制史上影响最大的朱熹《朱子家礼》对比,发现内容相近的内容有大约十五条。唐、宋、明、清四朝法典中的《户婚律》里,也有不少与《朱子家礼》中《婚》、《丧》篇相一致的内容。
那么从礼的角度该怎么看呢?上面提到的《礼记》中的《冠义》章里,有这样一句话:
敬冠事所以重礼,重礼所以为国本也。
冠事就是冠礼,也就是成人礼,是人一生中生、老、病、死的必经阶段,与家礼传统中冠、婚、丧、祭四种礼大体类似。照这种说法,重视了冠礼也就表示了对礼的重视,而这与国家的根本相一致。我们也可以倒过来理解这句话:国家的根本与每个人的成长息息相关,其中的关键环节,就是要重视礼,而这礼就落脚在属于“家礼”的成人仪式上。这跟《孟子》“天下之本在国,国之本在家”的思路完全吻合。
但礼和法在治国、治家的功能上,区分其实非常明确。《唐律疏议》有个雅致的比喻,说“昏晓阳秋相须而成”,意思是有晨昏才算一天,有春秋方是一年;这晨、昏、春、秋彼此相辅而相成,不可或缺。同理,“德礼为政教之本,刑罚为政教之用”,培育道德和养成礼节跟规定刑罚同样重要,都是施政和教化的必要环节,而且前者比后者更关键。只不过,随着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,家礼和国法各自担负的功能逐渐有了分工。一家的礼仪不能对本家庭以外的成员施加强制性的规范,国家大法也不可能、也没必要对所有的家内生活都做出规定。两者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,扮演了不同的角色。
可以说,家礼自身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。“德礼”被并列,虽然不是《唐律疏议》的发明,却透露了“德”是礼的重要基础这一信息。《论语》中有这样一句话:
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
意思是说,如果仅仅靠刑罚来管理国家,百姓虽然不会犯法,但在心里却没有对犯过错的羞耻感。从国家的角度,只有先用德育,再用礼来约束,百姓才会意识到羞耻和过失,才能免于犯错。
除了“德”,南宋大学者朱熹还提出家礼应该建立在“守名分”和“实爱敬”的基础上,冠、婚、丧、祭只是家礼的表现形式。名分就是人伦秩序,是对自己而言,爱敬则是针对他人。也就是说,在明确了个人的身份、角色之后,又能对他人充满爱敬之心,人们在家庭内外的言行就能得当,社会上才会礼风盎然,文质彬彬。
正因为朱熹的家礼理论包含了对己、对人两方面,又给了后来人以思考、补充的空间,因此有力地推动了家礼成为社会行为准绳。他的女婿兼学生黄幹说,朱熹的家礼规范既是“天理之自然”,也是“人事之当然”,我们怎么能不遵守呢!
但目前留存下来的家礼文本和仪式,并不是丝毫不变地延续它最初的样子。家礼也有个随着历史发展而演变的过程,在这过程中,产生了数量非常多的家礼著作,这完全与中国是礼仪之邦的美誉相表里。
谈家礼的书最早出现在先秦,但大多文字片段,不成系统,多被保存在经典中,在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中都有。后来经过《孔子家语》,逐渐发展成熟。到了六朝,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家礼著作——颜之推的《颜氏家训》。
魏晋六朝时期,谈家礼的书非常多。目的不仅是为了规范家人,还有彼此彰显门风的文化意味。到了唐代,社会稳定繁荣,规范家训、家规、家风的著作就更多了。但当时还主要是社会名流撰写,像杨炯《家礼》、李恕《戒子拾遗》、狄仁杰《家范》、姚崇《六诫》、李商隐《家范》等等,老百姓受到的影响很小。
到了宋代,家礼经过北宋司马光《书仪》、《家范》和南宋朱熹《朱子家礼》的调整和简化,逐渐成形。据《宋史·艺文志》统计,仪注类图书有171部,3438卷。作者有韩琦、许洞、司马光、吕大临、张载、程颐等著名士大夫。其中,《朱子家礼》成了后来传统家庭通礼的范本。
到了明清时期,家礼文献空前繁荣,内容也更加丰富。这期间政府的支持给了家礼传播以很大的推动力量。在明朝初年,《家礼》被编进了《性理大全》,与《六经四书集注》一起被颁行天下。与此同时,家礼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,有的虽然以书信的形式表现,但各篇积少成多,从整体上看,蕴含的思想体系却非常完整。翻看康熙朝编成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会发现,书中收录了大量的家礼和家规文献,其中《明伦汇编》有31部、116卷,《闺媛典》有17部、376卷。到了明代,能统计到的家礼文献有160部之多。
这些书虽然都属于家礼文献,但书里的门类划分还彼此不太相同。通行的编纂方法是从此前的典籍里选择同类文献,有时加上注释和辨析的话。例如南宋刘清之的《戒子通录》,就是南宋以前的家训集成。只不过编者按自己的分类,依照年代顺序,给重新编排了。他还附上了原作者的介绍和引用材料的出处,表明摘抄的并不是自己的话,但能表达自己的观点。
元代的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》是按照天干分卷,内容非常广,除了收录历代家训名言、读书治学、立身正己的方法,还包含了农事和饮食等内容。这种体例安排,被后世学者称赞为非常简洁。
清初窦克勤编写的《寻乐堂家规》分了祀先、子职、兄弟、夫道、妇道、妇变、教儿、教女、勤业、俭用、远别、睦族、友道、乡仪等14章。该书的涵盖面也广,被认为是家家可以通行、人人都该读的重要家礼著作。
大学者纪晓岚的哥哥纪昭编写的《养知录》,就是摘抄之前典籍中有关家礼、家规的内容。他是这么分类的——论事父母舅姑(也就是夫家的公婆)、论别夫妇内外、论处兄弟妯嫂、论教子孙、论厚宗族、论御奴仆、论制财用,最后一部分是通论大旨。王世俊在《闲家编》中,也是选择摘抄古人的说法。他开列了家训、家礼、家政和家壶四门,下面再各立子目,逐条抄录。
晚清著名的律学家汪辉祖的《双节堂庸训》分了六卷,共计列出219条训诫,分别谈“述先”、“律己”、“治家”、“应世”、“蕃后”、“述师述友”,详细告诫子孙为人之道。但著名书法家傅山的《霜红龛家训》就侧重在读书治学,并没有涉及迎师待友这类社交活动。
谈到这儿,我们可以对传统中国的家礼文化形成这样的初步认识:家礼并不是各家自己的事儿,它有个通行的准则和做法,历史上被有延续性地执行着。这做法在先秦时代就已产生,但直到宋代,经过司马光、朱熹等大学者的调整和规范,才形成了后来一直沿用的家礼范本和操作流程。
虽然家礼规定的是家中事务,对象是家庭成员,但跟国法在道德和行为上有着同样的高要求,承担着对人生之初的行为规范功能,也约束着人在社会活动以外的家内生活的点点滴滴。原则是要符合自己的身份,也要对人心怀爱敬,不逾矩,不出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