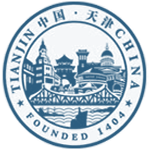历史上的家礼究竟跟我们有多大的差距呢,还能为现代社会所用吗?算一算朱熹在司马光《家仪》的基础上制定《家礼》,距今已经是八百多年前的事儿了。别说其中有的字如今不太明白,对其中的规定和做法,更有些费解。《家礼》中一个叫“曲裾”的部分,原文是这样的:
用布一幅。如裳之长交解裁之,如裳之制,但以广头向上,布边向外,左掩其右,交映垂之,如燕尾状。又稍裁其内旁大半之下,令渐如鱼腹而末为鸟喙,内向缀于裳之右旁。
可能在研究古代礼制和服饰史以外的人士,很难跟上朱熹对制作程序的解说。有人说,咱们不明白,是因为现代白话文和古代汉语有区别。其实,古人也存在跟今人同样的问题。因此,在南宋以后的各朝各代,也都有人因为不太理解《家礼》中的规定,或是因为觉得太烦琐、做不到,而提出该进行一些实际的改革,好让大家都能切实照做,保证家礼的实际效果。
在如今保存下来的陕西一份吕氏家谱(《(陕西临潼)相公庄吕氏家谱》)中,编者就提到,朱熹根据古礼,制定了《家礼》,在后世也确实被遵照执行。到了明代,有宋纁和吕维祺这位本家分别撰写了《四礼初稿》和《四礼约言》,对《家礼》删繁就简,好让普通百姓家都能遵守。
但到了这份家谱编纂的咸丰年间,家礼的规定在操作上又出了问题。问题仍然出在“仪文周详,节目繁重,人苦其难”上,也就是说当时的人还是觉得规定太烦琐、程序太多,超出了人们的普遍承受能力。而且,这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普通百姓家,即使是文化水平、社会地位高的士大夫家,也一样觉得太难办到了。于是,这个吕家想到一个解决的办法,就是斟酌古礼,继续将其中难以做到的部分删繁就简,设计成仅仅针对吕氏一家的家礼,编成了一部仅供自家人阅读的新书。这样一来,既保证了家礼有了执行的范本,而且礼仪和民俗之间也不会发生冲突,天理人情都照顾到了。何乐不为!
但从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跟吕家一样来看,这个历史上的老难题其实很不好解决。“礼”毕竟不是法,虽然也包含了对言行不当的惩罚措施,有强制性和和规范性,但怎么说都是管的法外的事儿,而且,还要本诸民情,合乎时宜,需要不断调整,使彼此相适应。如果做了大家都抵触的规定,对礼的普遍化和百姓文明程度的提升,也都无益。况且,从调整规范和适应民情的角度,法也给礼树立了榜样。《唐律疏议》中的“律”,就是在各朝既有连贯性,也有调整的内容。对此,需要再做一点儿解释。
“律”是传统中国历代法典的主干,律是汉代“律、令、科、比”结构中的主要构成要素,在唐代的“律、令、格、式”结构中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,在明清两代的“律、令并举结构”中仍然居于核心地位。也就是说,从唐代《唐律疏议》延伸下来,直到明、清的法典中,“律”的核心地位并未动摇。因此,我们谈到的唐、宋、明、清法典中的《户婚律》,有很多是与朱熹《家礼》中《婚》、《丧》的内容相一致,才有了比较的意义。但核对历朝法典就会发现,其实“律”也是有变化的,在各朝律例的宽严之间不断有调整。与之同理,家礼是否实用有效也体现在礼文的增删中。
其实,从朱熹开始,调整传统家礼具体做法的例子非常多。可以说,务实性是朱熹本人修订家礼的一个基本原则。我们来看看《朱子家礼》中的《婚礼》。这一章是以《仪礼·士婚礼》为基础进行改造的,具体有这么几点:
第一,删除了一些程序。将《仪礼》中的“问名”、“纳吉”、“醴宾”、“请期”、“飨送者”等都删除了。第二,合并程序。将《仪礼》中的“妇至”归并入“亲迎”;将“妇见”、“醴妇”、“妇馈”、“飨妇”归并入“妇见舅姑”;将“祭行”、“奠菜”归入“庙见”。第三,简化程序。将《仪礼》中复杂、重复和不合时宜的程序进行简化。第四,增加程序。朱熹新增了“议婚”和“告于祠堂”这两项。新人在祠堂里向祖先汇报婚事,不仅增加了婚礼本身的庄重性,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婚姻关系的稳定——既然祖宗都知道了,两口子的小日子就要过得踏实,否则可是无法向祖先交代的——还向祖宗表达了感恩之心,也表示了要延续宗脉的家族观念。第五,吸纳民间婚俗的内容。朱熹注意到了民间婚俗的力量,于是将“铺房”、“言定”吸纳进了家礼。
关于“议婚”,朱熹认可司马光的看法,要考察即将成为夫妇的双方的“性行”——请注意,这是包含性格和品行两个意思的词——再加上家里的“家法”如何。朱熹的意思,并不是要弄清楚家法是不是森严,而是要打听家里的规矩是不是严格,也就是家教好不好。这比光看男方家资是不是殷实,要有把握得多。对此,朱熹做了解释,他说男方即使现在贫贱,但如果品行贤良,怎么知道他将来不会富贵呢;相反,如果男方人品不肖,现在虽然富盛,难保将来不会落入贫贱。因此,他的看法是唯有性格和品行都好,才能确保家庭的稳定、和谐。
朱熹对女方家资是否殷实和新家庭能否和谐的看法,在当今社会也有借鉴意义。他说一家的女主人是家庭兴衰的关键人物,如果男方选择配偶时,只顾贪恋女方的财产而成了家,但对方仗着自己出身富贵之家,难免“不轻其夫而傲其舅姑”,也就是轻视丈夫甚至公婆,养成了骄纵之气,家内事务肯定不好处理。退一步说,即使借着女方家里的财力和势力富贵了,难道心中就没有愧疚吗!
新增的“铺房”环节,也是朱熹顺应民情的结果。“铺房”就是在婚礼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摆在床上,是当时百姓炫耀财富的手段,彼此还形成了攀比之风。但朱熹规定,铺房只需要铺设被子、毯子、帷帐等床上用品,其他用品如衣服、饰品等,一概锁在箱子里,不许拿出来陈设,以减少攀比。这跟刚才提过的别光看配偶一方家资是否殷实的基本思想,其实完全吻合。
明代的例子就更多了。出身河南,在山西、山东都做过地方最高领导的吕坤就曾经在任上表示过,家礼虽然节文详密,足以检讨人情,但礼仪的规定太过繁琐,反而会影响行礼者的忠诚之心和可信度。因此,他提出了个大胆的说法:家礼是家庭成员应该遵守的礼,但每家的礼可以不一样。
吕坤的说法虽然在清代有很多人批评,但他的做法确实有可取之处,而不能教条地认为他反对家礼的统一性。举个例子,吕坤对家礼中祠堂的位置的硬性规定,有不同意见。他说按照周礼井字的划分方法,祠堂在“正寝之东”,但如果家资并不殷实,辟不出一块单独的地方,就不能强求。可以在居室中间,设香案,垂下帘帐,作为代替。吕坤进一步解释说,如果这样做被批评为“非礼”,是没有道理的——如果坚持古礼的做法,又做不到,反而会导致祭祀之礼无法执行的更坏结果。(《四礼疑·通礼》)
吕坤还提到,当时北方的风俗是一年里朔望要焚香四拜,四季和冬至要五次祭拜,再加上春天的正月、夏天的四月、秋天的七月、冬天的十月,父母的生日和忌日四次祭拜,还有生孩子和冠婚丧祭等节日的仪式,加起来“一岁不减二十祭荐”。吕坤担心这么多仪式,“但不知家家能如是否乎”?既然不是每家都能完成,那表达爱心和慈善就成了空话。因此,适应性的改革和调整成为必需。从如今保存的文献来看,吕坤和他同时代的学者,根据山西、山东和河南的地方风俗,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。
对这些学者调适家礼的努力,虽然后世评价的态度不一致,但他们精简家礼环节,使仪式适应地方实际状况,进而保证其实用性和效果,对中国传统家礼文化的传播和延续,是有重要贡献的。
但有一点值得提醒的是,虽然很多地方都有对家礼内容的调整和改易,但从文献中来看,各家的态度还都十分谨慎,说辞也都尽量周全。例如清代同治年间的一份王氏族谱(《湘潭兰下王氏四修族谱》),就说司马文公的《家范》、朱文公的《家礼》当然是百世不易的,但“时俗不无异尚,乡曲或有难行”,与其成为操作上的空文,不如斟酌时宜,将各种规范落于实处。而这是“因乎情,起乎义”,从于宜的。也就是改变要有理论基础,不能信手就改、随意即变,这其中的根据,就是我们曾经谈到的“德”、“名分”和时宜等元素。类似的说明文字,在明清两代家谱、族谱、宗谱中常见,可见,历史上的有识之士一直都注意着规定和执行上的偏差与统一的问题,并一直给后人提供着成功的典范。